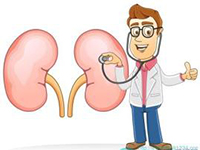慢性腎炎的治療經驗及用藥心得
慢性腎功能不全、慢性腎炎等慢性腎病,是常見而難治的慢性腎臟疾患。臨床以水腫、蛋白尿、血尿、高血壓為等特征。慢性腎炎的病因和發病原因,目前尚有爭論,但大多醫家認為,本病是一種與感染,特別是乙型溶血性鏈球菌感染有關的免疫反應性疾病,現代醫學對本病尚缺乏較理想的療法。
根據慢性腎炎的臨床表現,在中醫學的水腫、虛勞、腰痛、眩暈等病證中有類似記載。由于慢性腎炎后期全身機能衰退,出現氣血陰陽虛衰現象,極似中醫學的“虛勞”癥狀。慢性腎炎的高血壓證型有類似中醫頭痛眩暈等病證。古代醫家都從不同角度對本病已有較深刻的認識。但對本病的診斷方面,中醫是有不足的地方,特別是一些表面癥狀不明顯的病人,通過中醫診斷是不行的,必要通過西醫的腎功能檢查才行。很多病人通過吃一兩個月的藥,很多臨床表面癥狀都消失,以為病好了,再通過腎功能檢查,發現尿里還有++以上的紅細胞、尿蛋白等,說明了病還沒有全好,如果不連續治療,病情還是會復發的。所以中西醫有必要結合起來,不能過分的迷信中醫。
對本病的治療本人稍有體會,認為本病的發生是由急性腎炎沒有得到合理的治療,沒有完全治好形成的。急性腎炎后身體會虛弱,風寒、風熱、熱毒、濕熱等病邪反復入侵;病久了情緒也不好,影響了氣血的暢通。飲食方面不節制,酒色勞倦等各種因素造成臟腑(特別是肺、脾、腎三臟)虛損,功能失調,使體內水精散布及氣化功能發生障礙,臟腑日益虛損,而外邪反復入侵,導致臟腑之間、正邪之間的惡性循環,形成了慢性腎炎反復發作,長期不愈的臨床特點。風邪外束,肺氣不宣,肅降失司而成風水,遷延不愈;導致脾腎陽氣虛衰,水濕潴留或泛濫發為本病。腎氣不足素體腎氣不足或房勞過度,勞倦內傷,腎氣受損,開合及氣化功能失調,腎氣不能化氣行水,水氣阻滯,溢于肌膚而外見水腫;腎陽不足,不能溫煦脾土,運化功能失司,水濕不能輸布,脾土既虛累及肺金,肺氣通調無權,水氣失于宣降。肺、脾、腎三臟柏互影響,導致本病遷延日久,難以治愈。若腎陰下足,水不涵木,肝陽偏亢,則可導致水腫眩暈并見的臨床癥狀。此外,肝失疏泄,氣機不暢,氣滯血瘀,也可致使本病癥情復雜而難以治愈。
對本病的診治有很多人都以分型論治,但本人認為此病的臨床癥狀多樣,在中醫很難歸于哪一種病證,在水腫、腰痛、虛勞、關格、嘔吐、衄血等病中都可見本病的癥狀描述,但是不全面的,應根據每個患者的不同情況辨證論治。本病為虛實夾雜證,由于每個患者正虛與邪實的情況不同所出現癥狀亦不同。按辨證本病病變過程中,皆表現為虛實夾雜,本虛標實,本虛以脾腎虛衰,氣血陰陽皆虛;標實以濕、瘀、毒潴留,但每個患者在病變過程中所表現的本虛標實的程度各不同。一般在病變進展時多表現以邪實為主,治時以祛邪為主佐以扶正;如在病變相對平穩時,多表現以本虛為主,診治時則扶正為主佐以祛邪。盡管每個病例虛實的情況有不同,但治療時應虛實兼顧,分清標本緩急按正虛和邪實的不同情況,補虛與祛邪的側重點有所不同,靈活用藥才能取得療效。
臨床中見病人全身水腫明顯,尿少,面色蒼白,身重倦怠,胸悶,腹脹,食欲減退,腹瀉,舌淡苔薄,脈濡弱。此為脾腎陽虛,治療應益氣健脾溫腎,佐以通利水濕、化瘀解毒。藥用黃芪、白術、茯苓、豬苓、防己、澤瀉、桂枝、肉桂、仙茅、仙靈脾、巴戟天、菟絲子等治之,固本方面以健脾為主,溫腎為輔,如單一健脾不加溫腎,則脾陽不溫效果不顯著。特別是黃芪一藥,本人臨床運用治療本病,不論是尿血、尿蛋白出現,得重用,一般用到100-300克一劑,效果很好。氣虛嚴重,必會至陽虛,對于腎陽不足自從《傷寒論》中用四逆類湯后,后世醫家一直都從這一思路去用藥,本人從臨床中看,只溫陽,效果不好,還得以大劑量的黃芪加四逆湯,以補氣為主,溫陽為輔,效果要明顯增加。
如有頭痛,頭暈,耳鳴,腰i乏力,五心煩熱,口苦咽干,大便干結,小便短赤,面色晦滯,舌形較小,舌色暗紅,苔少或薄黃,脈細弦或細數。此為肝腎陰虛,治以滋養腎陰,平肝潛陽。藥用生地黃、枸杞子、丹皮、甘菊花、黃柏、知母、制大黃、玄參、旱蓮草、白茅根等藥,特別是白茅根一藥,對于血尿的控制非常好,但得重用,干藥得用到100克以上,有條件的話,最好是用鮮的。陰虛則血脈不充,血必不暢,生地黃《神農本草經》記載有“除血痹”的功能,所以對于陰虛嚴重的病人來說,要重用生地黃,每劑可用到300克。現代藥理研究,地黃有類激素樣作用,對于本病在用激素治療的,又沒有激素的副作用,通過大劑量用地黃可以較順利的撒激素。頭痛嚴重的是陰不養肝,肝火太旺,加鉤藤以平肝;熱得嚴重了會手足抽搐,加羚羊角粉、生牡蠣涼肝鎮肝;齒衄、鼻衄加仙鶴草、側柏葉;尿血加白茅根、小薊;便血者加地榆碳、槐花碳等。
如見全身水腫,皮疹癢或有濕疹、皮膚感染,尿少而赤,有尿痛,舌苦黃膩,脈濡滑數,此為濕熱壅滯嚴重。治療應治標為主,清熱利濕。藥用白花蛇舌草、蟬衣、蒼術、黃柏、苦參、地膚子、白癬皮、銀花、連翹、生米仁、益母草等。對于這種情況,米仁效果很好,必重用,每劑藥用到300克以上。如病人水腫消退或無水腫而以蛋白尿為主者,此為脾虛運化失司、清陽不升、水谷精微下陷;腎虛封藏失職、腎不藏精則精微外泄。此多為病情的平穩期,治以健脾益氣,補腎填精,佐以固澀,藥用生黃芪、太子參、白術、山藥、蓮子、扁豆、芡實、金櫻子、桑螵蛸、白果、沙苑子、覆盆子、龍骨、牡蠣、三七、仙鶴草、枸杞子、山茱萸、女貞子等。
本病纏綿難治,熱毒壅盛、濕熱纏綿、瘀血阻滯等是標癥中突出的矛盾,治療時在扶正固本的基礎上,必用清熱解毒、清利濕熱、祛風勝濕和活血化瘀以治標,要不體虛永無法補。清熱解毒法主要是針對上呼吸道感染、扁桃體炎、皮膚感染等熱毒壅盛而誘發和加重慢性腎炎病情的情況。初發多兼風熱,日久則易傷陰,可根據不同感染部位進行加減選藥。如伴咽炎、扁桃體炎,可用金銀花、野菊花、蒲公英、紫花地丁、黃芩、蟬蛻、僵蠶、連翹、蚤休、桔梗、牛蒡子。傷陰者加生地黃、玄參、麥冬、沙參。伴皮膚感染,可加丹皮、赤芍、白蒺藜、地膚子、白鮮皮、苦參、蛇蛻。伴胃炎、腸炎加黃連、馬齒莧、葛根、地錦草等。伴肝炎可加柴胡、茵陳、雞骨草、虎杖、苦丁茶、金錢草。
慢性腎炎纏綿難愈反復發作,除責之于脾腎虧損外,濕熱病邪亦已成為突出的矛盾。在慢性腎炎伴腎功能損害過程中,濕熱是貫穿始終的病邪,用藿香、豆豉、竹葉、滑石、杏仁、橘皮、黃連、半夏、枳殼、厚樸、茯苓、茵陳、草果、萆薜、車前子、玉米須、米仁等藥,擇而用之。對于濕邪久留,脾氣被困,應用芳香化濕、苦辛燥濕、淡滲利濕等均告無效時,可用祛風勝濕法,取風能勝濕之理,用苦辛溫散、祛風除濕之法,以達濕邪祛除、脾運舒展之目的。可選用羌活、獨活、藁本、麻黃、桂枝、荊芥、防風、青風藤等。雖服藥后汗出并不明顯,但外感明顯減少,自覺周身溫和舒適、飲食增加、浮腫消退。中醫謂久病必有瘀,葉天士“初病氣結在經,久病血傷入絡”,并指出“絡以辛為泄”,本病病情長久,濕瘀毒互結,脈絡瘀阻,治療時必須要適當的加入活血藥,如當歸、赤芍、川芎、丹參、桃仁、益母草、虎杖、澤蘭、劉寄奴、川牛膝等。如病情嚴重,久病人絡,頑痰死血留而不去,此時一般活血化瘀藥如丹參、川芎等療效欠佳,則用蟬蛻、僵蠶、白花蛇、烏梢蛇、蛇蛻、穿山甲、地龍等蟲蟻辛咸之品,深達絡脈以搜剔頑痰死血。蟲類藥的使用當分輕重,輕者用僵蠶、地龍,中度可加全蟲,重度再加蜈蚣、烏梢蛇,以循序漸進,不可過猛,以免耗傷氣陰。用量應由小漸大,視患者體質和病情逐漸增加,取得療效后又應逐漸減量直至停用。
臨床如見泛惡嘔吐,納呆尿少,面色暗滯,浮腫,口穢或膚癢,出血,神昏,抽搐等癥,甚至頻繁嘔吐,化驗單見肌酐,尿素氮持續升高。此乃濁陰上擾之侯,類似祖國醫學中之“關格”癥侯。此時病情危篤,服藥困難,必須采取大黃、徐長卿等中藥保留灌腸,有必要和西醫配合起來治療,全力救治,保命第一。待病情穩定后再采用其它治法。
對于本病病情的輕重不同療效也不同,臨床中以脾腎虧損,氣血兩虛證,濕濁瘀毒阻滯,病情相對要輕些,治療效果要好些。如證見是肝腎陰虧,肝陽上亢,濕熱毒蘊結的多是病的后期(很多病人都是服利尿藥、激素藥而傷陰),病情多較重,治療也很是棘手。如病情發展到慢性腎衰是難治之癥,特別是后期病情危重,不易治療,須采取綜合措施,多途徑給藥。慢性腎炎是引起終末期腎衰(尿毒癥)的第一位原因,西醫無很好辦法,對比較頑固的蛋白尿等癥狀,只能采取激素等進行維持性治療,患者容易反復發作,有必要結合中醫的固本扶正治療。
此病病程長,治療不易速效,須堅持長期系統治療,若缺乏耐心,急于求成而雜藥亂投,往往導致病情反而迅速惡化。另外根據《內經》“勞則氣耗”、“因而強力,腎氣乃傷”,《脾胃論》“形體勞役則病”,進行患者自我調攝十分重要,生活要有規律,調節情志,不要過度勞累,多休息,注意寒暖,避免感受外邪,飲食要合理,清淡而有營養,要及時進行規范治療,防止出現腎功能衰竭。療法力求平穩,處方遣藥要分清主次緩急,切忌猛劑躁進苛烈攻伐之品,恒選穩中取勝之道。陰虛患者慎用激素治療,以防加重濕熱癥或陰虛癥。辨證施治時,應做到客觀檢查數據與整體觀察相結合,力求準確無誤。祛邪應做到中病即止,時刻注意顧護真陰真陽,因正氣一衰百藥難醫。本病雖說以虛為本,但不能蠻補,要補而不膩,能守能通,有寓通于補之意,可以久用,才能收到應有的臨床效果。
- 上一篇:腎小球腎炎有什么特效藥呢
- 下一篇:慢性腎炎治療用藥經驗介紹
相關文章
- 治療腎炎的藥方
- 腎炎吃中藥能治好嗎
- 腎炎患者怎么用藥?
- 狼瘡性腎炎的用藥
- 中藥治療腎炎
- 藥物治療腎炎是不是真的有效
- 腎炎如何用藥
- 狼瘡腎炎免疫如何用藥?
- 慢性腎盂腎炎治療用藥經驗
- 中藥怎么治療紫癜性腎炎
- 腎炎患者如何安全用藥?
- 紫癜性腎炎常用哪些藥物?
- 熱門閱讀
免費提問